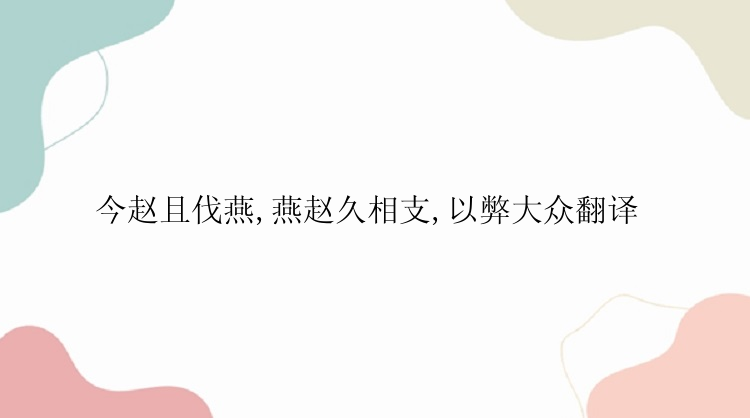对于厌食症患者来说,美食不再是一种享受,而成为一种折磨。每次面对精心制作的美味佳肴,他们看到的只是卡路里和脂肪含量,而不是美味和享受。对他们而言,进食不再是满足身体需求的过程,而成为一场心理战,不断挣扎在恐惧和渴望之间。食物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滋养和慰藉的象征,而是一种惩罚和自我控制的工具。

文 刘旭
莉莉·柯林斯主演的电影《骨瘦如柴》剧照。该片讲述了患有厌食症的艾伦在医生的帮助下与厌食症作斗争的故事
控制体重本来是为了享受身材变得纤细的快乐,但过犹不及,在魔鬼式减肥后,失去脂肪的同时,快乐的能量与力气似乎也消失了。起初,是你主动控制体重与饮食,而最后,往往是你成为那个被控制的人。
以下是两个曾因过度减肥而患上厌食症的女孩的经历。
范文琪:为什么好好吃一顿饭
会变得如此艰难?
范文琪天生有副好嗓子,歌儿唱得极为好听。上中学那几年,每年的校园歌手大赛的获奖名单里必定有她。因名字近似于歌手范玮琪,所以同学们叫她“一班范玮琪”。不过在这个看似褒奖的称谓之前,人们习惯性地加上“胖版”或者“大号版”的限定词。对范文琪而言,“那是一种夹杂着羞耻感和痛感的体验”。
高二上学期,她决定减肥。每天早上,她吃两个水煮蛋和半截玉米。鸡蛋只吃蛋白,而蛋黄则被她当成“发泄的工具”——她用不锈钢小勺将其碾碎在盘中,而后像倾倒碎末一样丢进厨余垃圾箱。“那时我很需要解压,一方面是来自学习成绩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想快点儿瘦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别人对我的闲言碎语了,哪怕是无意中说的一句都不行。”
到了午餐时间,范文琪会先去开水处接上一小碗水,“为了涮掉菜上的油”。她通常会点两个素菜,实在觉得馋了,才点一份肉菜,“鸡肉或者牛肉,猪肉从来不点,因为太胖人”。点好菜之后,她会窝在角落,细致又审慎地去掉菜上挂着的油星儿,之后再填进嘴里,机械性地完成咀嚼和吞咽。
有几次,“实在没躲过去”,她和同学下了体育课后一块儿到食堂吃饭。同学见到她的吃法后,问她,这能好吃吗?她支吾着说:“还行,主要是能减肥。”同学模仿她的样子,咂摸了几口,差点儿没吐出来。范文琪当时觉得很受刺激,自那往后,她再也没和人一块儿吃过饭。
对范文琪来说,晚自习之前的时间是最让她幸福的。由于休息间歇短,所以很多人在晚餐上都是应付。她至今记得那种感觉,太阳西下,橙红色的日光斜射进教室,有人在啃面包,有人在吃烤冷面,只吃几颗红枣的她,一点儿都不显得奇怪。
饮食上极为苛刻的她,短时间内收到了非常好的成效。5个月不到,身高164厘米的她体重减少了十几公斤。但随着体重的变小,她感觉“脑容量好像也不如从前了”。在课上,她的注意力很难集中,每次走神儿,脑子里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好吃的窜出来。为此,她准备了一个私密的笔记本,专门用来画画。只要一有念头,她就迅速画下有关食物的简笔画。
课下,她的记忆力也有受损的迹象。语文课本上要求“背诵并默写”的篇目,她怎么努力都记不下来。几次考试的成绩也都“往下滑,无一例外”。老师找她谈话,她耷拉着脑袋,一声也不吭。“我大概明白是咋回事儿,但没法跟她说,她不会理解。”她低下头时,瞥见老师细长有型的腿,她想的是:等放暑假,我也能穿这样的丝袜。
但等暑假回家,范文琪实在绷不住了。她开始暴饮暴食。父母不了解情况,还以为是学校的伙食太差,于是俩人分工协作,一个买菜,一个下厨,变着花样地给闺女做顺口的菜。在餐桌上,范文琪狼吞虎咽,父母嘱咐她“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但她完全控制不住,“我也并不是享受食物本身的味道,我只是想吃,想完成这个动作而已”。
可吃完之后,她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有时候到了半夜,她觉得食物在腹部沉积,就猛嚼管消化的药片,然后跑出家门,去离家不远的广场快步走。父亲不放心,会尾随着她出去。他看见范文琪在广场上一边大哭一边踱步,他也不知道咋回事,又害怕生性敏感的孩子多寻思,没过问。他觉得,孩子大概是压力大,想找个出口吧。
2020年8月21日,深圳,四季酒店。大多数女孩以身材纤细为美,减肥成为她们的人生必修课。(图/阿灿)
回到学校,范文琪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像上一学期那样执行“魔鬼饮食计划”了。两个月体重反弹了将近10公斤的她开始在网上找其他方法。“哥本哈根减肥法”“郑多燕操”“哪一款减肥药效果好”,那段时间,范文琪的浏览记录里充斥着这样的关键词。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一个群体,叫“兔子”。
“兔子”的成员年龄跨度很大,最小的14岁,最大的40岁,以女性为主。虽然人生阅历完全不同,但她们有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在减肥的同时还能无限度地享受美食。于是这群人每天用抠喉的方式把吃进去的食物吐出来。她们渐渐形成一个组织,其间不乏一些黑话:比如“吐”,她们叫“生”;“暴食”,被称为“撸”……
范文琪似乎找到了新的减重路径,她依循帖子里说到的方法,吃了吐,吐了再吃,毫无顾忌。没过几个月,她的体重再度降了下来。每每身边的人对她的身材变化感到讶异时,她会产生一种“畸形的自豪感”。她说:“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时,我会感到快乐,虽然明明知道那是不健康的。”
与之相伴的问题是,每次吐完,范文琪都会觉得食道有一种难以忍受的酸蚀和烧灼感。为了避免产生这种感觉,她慢慢减少进食,直到一段时间后,她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在高二下学期,她休学了。
父母带她去哈尔滨的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在她的诊断单上,病症一栏赫然写着“进食障碍”和“中度抑郁”。父母不明白是啥意思,他们问大夫,为什么自己的女儿会讨厌吃饭呢?大夫解释之后,他们依旧发懵。
范文琪所患的病症属于精神类障碍。该组综合征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前者的主要特征是患者用节食等各种方法有意地造成体重过低,拒绝保持与年龄、身高相称的最低标准体重;后者则是反复出现暴食以及暴食后不恰当的抵消行为,如诱吐、服药、节食或过度运动等。
躺在病床上的范文琪,一边输液,一边回想着自己一年以来的历程。她有很多解不开的疑问:到底怎样才算是追求美呢?为什么好好吃一顿饭会变得如此艰难?还有,我想变成不带限定词的“范玮琪”,真的有错吗?
莉莉:无论吃什么,
眼前都会飘起一行数字
莉莉患上进食障碍,是在大二时。她的饮食习惯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她有过一天只吃一个鸡蛋灌饼的经历,也有一天点六顿外卖,每顿都吃到顶住的时候。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下,她的身体状态日渐变差,体重也比刚入学时增加了10公斤。
在闺蜜和家人眼里,莉莉原来偏瘦,胖了之后体形还算正常,所以莉莉对此也不以为意。有一次,在一个主打陌生社交的平台上,她发了张在厦门海边穿着比基尼的照片。一个和她聊了很多次的男生给她留言,说:“你人很漂亮,就是现在有点儿胖。”在“胖”字的后面,还有一个猪头的表情。莉莉觉得很受冒犯,于是“玩命地控制体重”。
她每天运动一个半小时,有氧和无氧交替着来。除了“迈开腿”,她还严格地“管住嘴”,她使用一款带食谱的软件,每种食物都被标注了热量。至今,她还能对很多食物的数值脱口而出。她说:“那段时间就像着了魔,无论吃什么,眼前都会飘起一行数字。”
在与体重的抗争中,她胜利了,她的BMI指数显示她处于偏瘦状态;但与身体的博弈,她却败下阵来。她开始大量掉发,“掉下来的头发,时常会把浴室的地漏堵住,那段时间,我对洗澡很恐惧”。此外,她的月经也开始和她“捉迷藏”,时来时不来的例假给她传递了危险的信号。
最让她痛苦的是,她察觉自己的食欲大不如前。莉莉以前爱吃韩国料理,但患病的时候,部队火锅、韩式炸鸡、芝士肋排,没有一样唤得起她味蕾的兴趣。她到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求助,辅导老师跟她聊了一下午,最后建议她去医院看看。
在北京朝阳医院,她被确诊为“神经性厌食症”,外加“轻度抑郁”。确诊后,莉莉开始服药,同时她也去图书馆找一些相关书籍来看。她希望能从学理上找到根源。“但书看得越多,心里反而越焦虑,我希望能找到一些人来交流。”
然而,和几个闺蜜的交流并不顺畅,“因为她们根本无法理解那种感觉”。那时,她深切地意识到,在“厌食”这件事情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你们的所谓美食,对我来说其实是种折磨”。
找不到人倾诉的莉莉试图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共鸣。她说:“我看过一千多部电影,最有感触的就是《骨瘦如柴》。”原因很简单,那部电影中,有和她一样厌倦食物、恐惧进食的人。于她而言,《骨瘦如柴》复刻了她过往的生活印记。
当得知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少年时为控制体重,也曾患上厌食症时,莉莉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摘录了一段格丽克的话:“厌食症带来的饥饿感帮我控制了贪欲,对于获得一个独立的自我,是大有帮助的。”她觉得,或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这个病症。
但莉莉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是,对厌食症的讨论相当匮乏。莉莉曾进入豆瓣、贴吧、微信等平台上的相关群组。她发现,这些群内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一些人在自说自话,一些人是无病呻吟,还有一些,是吃‘人血馒头’,宣传药品和心理疗法的”。
莉莉说:“我不奢求人们充分了解厌食症,但我觉得,这个死亡率高达5%—20%的精神障碍,需要被别人看见。每一个患上厌食症的人,都陷入人生的至暗时刻,我们需要得到‘救援’。”
持续进行心理治疗后,莉莉的病症有所缓解。她把自己的经验写了出来,发布在多个平台上。起初,互动的人并不算多,但坚持一段时间后,私信给她的人越来越多。她耐心地答疑解惑,不过,更多时候,她愿意作为一个倾听者。她相信,和自己一样的人,需要这样的倾诉机会。作为一个“过来人”,她充分理解厌食症患者的每一步选择。
和莉莉同校、差了三个年级的范文琪,就是通过这样的沟通与之相识的。如今,她们都不再受困于进食障碍。她们时常一起约饭,吃“网红”小馆,有时还会拍探店的vlog。当她们坐在一起时,很少会再聊与厌食症相关的话题。因为,对她们来说,那段经历意味着过去。但在未来,她们希望自己可以出一份力,帮助那些和她们一样的人。
以上就是厌食症患者:美食对我而言是一种折磨的相关介绍,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如果您还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方式,可以往下看看相关文章,有很多厌食症患者:美食对我而言是一种折磨相关的拓展,希望能够找到您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