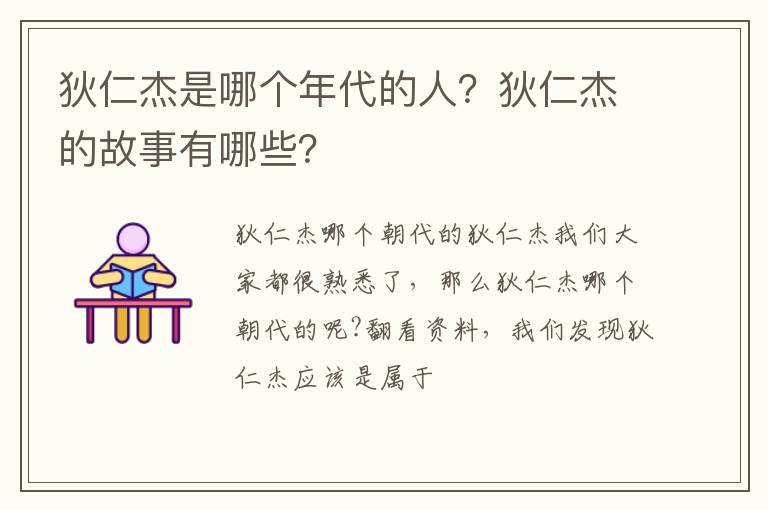康德是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在他300周年纪念日这一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们不禁思考:世界的更好状态从何而来?或许正是在我们对人类理性的理解和尊重上,我们才能够找到答案。康德的思想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自由和道德的理性选择,我们才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庆祝康德的成就的同时,让我们共同探讨,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2024年4月22日,是康德300周年诞辰纪念日,图为德国邮政部门发行的纪念邮票。
今天我们来纪念康德300周年诞辰。当我们提到康德,或当康德的形象或隐或显地在眼前晃动时,我们最能想起的是他的一句什么话或一个什么观念?我想可能各不相同。为什么?一是因为康德所论述的问题太多,所说过的话也太繁复,几乎无人能用一句话或几句话来概括他心目中的康德;二是当我们纪念康德300周年诞辰时,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存境况有着不同的感受,于是也就把这种感受转移到康德身上,想借康德的论述来表达出自己的某种心意。
这都很正常。但如果能更好地讨论一下,也许我们会相对地达成某种共识。这就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不是也应该如康德在《论教育学》中所说的那样去探讨:“那么,世界的更好状态从何而来呢?”(康德:《论教育学》,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9页)
他当然认为这个更好状态应该从教育的改良、知识的传播、灵魂的提升而来,而且,在他这句话前面,也一定说了些对当时教育有所不满的话。
其实也没有。他只是说,我们制定教育规划的人,不应该以人类的当前状况,而应该以人类将来可能的更佳状况,“即合乎人性的理念及其完整规定”为准来实施教育。这与康德对历史教材的看法是一致的,即我们渴望着有一部“并非有关过去,而是有关未来时代”的历史书,“此外,如果要问:人类(整体)是否不断地在朝着改善前进;那么这里所涉及的就不是人类的自然史(未来是否会出现什么新的人种),而是道德史了;而且还确乎并非根据种属(singulorum),而是根据在大地上以社会相结合并划分为各个民族的人类的全体(universorum)。”(康德:《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5页)
康德是一个永远着眼于人类全体的哲学家。于是在回答“世界的更好状态从何而来”之前,我们可以先这样概括一下这位大思想家的两大特征:第一,我们发现,康德是相信人类全体有着更好的状态的,正如他相信人类全体是在朝着不断改善的方向前进一样。尽管这只是一种概括性的,在动态、趋势、因果上的相信,而不是指人类社会具有某种统一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当然,就是这样,我们也必须如他那样问一下:这种更好状态从何而来?
相信人类全体有着更好的状态,就如康德也相信人类全体会有“永久和平”一样,这是不是一种乌托邦?
近些年,关于反乌托邦的论述已经很多。我也大都同意。但有一个问题需要区分一下,就是哲学是一门关于概念的学说,而概念需要释放它的内在含义,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也就是实现它的全部潜能。这确实是有关哲学使命的不同于乌托邦、但又与其有着内在关联的一个核心问题。概念如何释放它的内在含义?这就需要讨论,需要解释,需要为之做出言论上的努力,如自由、正义、平等、法治、博爱等等。这与历史的或概念的决定论、必然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又很可以讨论二者的关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文明,这许许多多的概念,我们的现实生活和言说空间能离得开它们吗?而且我们又怎么可能只满足于让这些概念只停留在观念上?所以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事实上是区分不开的。
第二,康德是一位每每都要先给自己所要讨论的议题下一个定义的哲学家。大的如“三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他都会在一开始的“导言”中讲清楚什么是他所理解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到《判断力批判》的“导言”的最后,康德干脆画出了一个表格,说明人的内心就只有三种能力:认识能力(面对自然的知性能力,其先天原则是合规律性)、感受愉快或不快的能力(艺术领域里的判断力,其先天原则是合目的性)和欲求能力(体现自由的理性能力,是人内在能力的终极目的),以此来说明“合目的性”的判断力“就使得从自然概念的领域向自由概念的领地的过渡成为可能。”(《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第422页,杨祖陶、邓晓芒编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小的如谈到什么是启蒙运动,也是先给“启蒙”这一概念下了一个人所共知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谈到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就给“历史学”下一个定义:历史学从事于对人类行为的叙述,不管这些行为的原因多么隐蔽,“但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把个别主体看来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禀赋之不断前进的过程,虽则是漫长的进程。(以上均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关于教育学,康德的定义更简洁、明晰:“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造物。我们所理解的教育,指的是保育(养育、维系)、规训(训诫)以及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据此,人要依次经历婴儿、儿童和学生这样几个成长阶段。”(《论教育学·导论》)
这些都说明了康德的一切论述,都是对概念的展开,他把这种展开也视为人类的某种原始禀赋的不断展现。这种原始禀赋就包括在三大批判中所要讨论的人的三种“内在能力”、启蒙所要解决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内在能力的自我遮蔽,以及历史学所要揭示出的就是人的内在能力在漫长历史时段中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
所以康德又是一个相信人的内在禀赋和先天能力的哲学家,并因此而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也因此又在表达信心的同时充满疑虑。这是一位整整活了80岁的哲学家,我们想要他前后一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也是18世纪以来整个欧洲处于上升阶段的某种普遍情绪。也许我们“真宁可在希望中出错,也胜过在绝望中说对”。那时候的思想家们,都普遍意识不到理性的有限和语言理解上的差异,以为靠理性的力量就能改变世界,问题只在如何把理性的力量(在康德看来,也就是人先天就具有的内在禀赋)唤醒、启发或者弘扬起来。这也是康德认为世界会走向一个更好的状态,因而也就特别重视教育的根本原由。在《论教育学》的第117页,他专门谈到了法国大革命。康德认为发生在那里的革命尽管可能很悲惨、很恐怖,但却在观察者心中激起了某种近乎热诚的同情,尽管这种同情表现的本身也带有风险。他认为这种同情有两大原因,一是权利,即一个民族为自己提供一种他们觉得对自己很好的公民体制,就不能受到另一个强权的阻挠;再一个就是目的上的原因(它同时也就是义务),即创造一个能防止侵略战争的体制,那就只能是共和制,这是一种得以防止战争(一切罪恶与道德腐化的根源)的条件。当然,当康德这样说时,是把自己仅仅作为一位观察者而不是一个被卷入这场演出的实际参与者的。而我们都知道,这二者所说出的话肯定大不相同:作为观察者,他只希望有关当局不要把他视为雅各宾派或暴民;而他,作为一名观察者,也并不想把已经具有了君主制的一部宪法改变为共和制。
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第2页,也就是《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一开始,他就注意到了人性之恶,或可称之为“根本恶”,即不是指具体行为的恶,而是让一切行为都合乎心中的“恶”的标准。他是这样说的:就人作为一个物种的全体而言,“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而成的”。但这一切,告诉康德的只是因此就更应该沉入自己的沉思生活,“根本就不能假设有任何有理性的自己的目标”,而是应该超出理性去思考某种自然的目标,“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这段话说不定与已经出现的AI,即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有关。这看起来已属于另一个也许更为恢弘,或更为恐怖的话题,但如果我们再联想到他在论述到人类的自然史和人类将来可能的更佳状态时,也设想过新的物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一个既着眼于人类全体和内在禀赋,又寄希望于启蒙、教育与知识的传播的思想家,其实也有可能设想过人类会成为一个,或被某种合乎自然计划的“新的物种”所取代?
这一话题其实是徐贲先生在《人文启蒙的知识传播原理》(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中提到的。他先说:“人们发明互联网,本意是希望大家多多交流,让思想越来越活络开放,然而实际上却只是让傻子们找到了彼此,成了更顽固的傻子。作为一个传播知识的媒介,互联网不但没能开启人们的思想,反而封闭了人的思想,因此互联网的实际作用与启蒙的目的适得其反。”(第312页)我们都知道,在康德看来,启蒙的个人障碍是懒惰和怯懦,如果再加上上面提到的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假设康德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会怎么想?徐贲先生说,“很难想象他会把‘信息太多’看成是一个问题,更不要说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了。康德从来就认为,就算是错误的知识也有它的作用,错误的知识的危害不在它本身,而在于人太懒惰,太怯弱,不能辨别那是错误的知识。因此,需要的不是禁止或消灭这世界上所有的错误知识——这是做不到的——而是让人们变得勤快、勇敢和聪明起来,学会如何辨别错误的知识”。(第334页)但又如何让人学会辨别错误的知识呢?还是得启蒙,得把人先天就具有的内在禀赋唤醒、启发或者弘扬起来。于是我们就又回到了开始。当然,网络知识不是书籍知识的数码化,而是出现了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知识生成机制;现在的AI,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也正在从根本上动摇着康德所告诉我们的“人类全体”和“内在禀赋”。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如徐贲先生所言,康德当然还是会把“勇于认识”作为自己的旗帜(第337页),而且要加上“善于认识”。我们也承认“网上的暴民并不是互联网的必然新政治形式”(第336页)。但康德哲学如果丧失了他的全体性、内在性和先天性,他的哲学体系还能构建起来吗?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如果没有康德的三大批判,《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和《论教育学》,我们还能意识到自身的懒惰、怯懦,愚蠢、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吗?问题当然在于:就是意识到了又能怎样?继续沉下心去思考自己的问题吗?自己的什么问题?
陈家琪
责编 刘小磊
以上就是康德300周年纪念:探讨“世界的更好状态从何而来?”的相关介绍,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如果您还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方式,可以往下看看相关文章,有很多康德300周年纪念:探讨“世界的更好状态从何而来?”相关的拓展,希望能够找到您想要的答案。